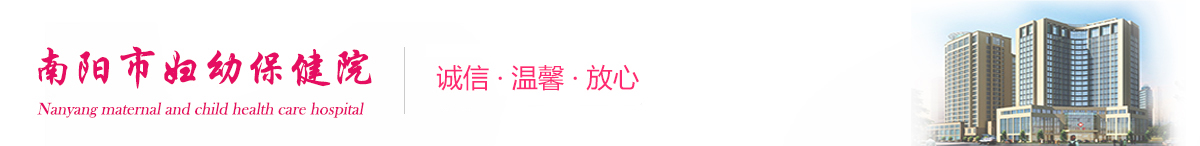
生殖是人类生存延续的永恒主题,配子的正常发生、成熟、输送、结合、种植和生长是人类得以繁衍的物质基础。人类许多生殖细胞适应生理过程发生程序性死亡,但由于近代环境污染等各种因素的作用,这种程序性死亡过程正在加剧,使生命之源的产生发生障碍,配子结合无能,生殖活动被迫终止。为了延续生殖过程,在了解生殖过程的基础上,在其发生障碍时给予医学的帮助,由此产生一门新兴技术――辅助生殖技术。
辅助生殖技术(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ART)是指所有涉及体外操作人的卵子和精子或胚胎,以达到妊娠目的的方法。按照这个定义,1790年John Hunter将一位尿道下裂患者的精液采集后注入患者妻子的阴道内使其成功妊娠,即夫精人工授精(artificial insemination by husbandsemen,AIH)以及1844年 William Pancoast用一位捐赠者的精子使一位妇女妊娠,即供精人工授精(artificial insemination by donor semen , AID),也属于ART的范畴。当然学术界一般以1978 年世界第一例试管婴儿——体外受精及胚胎移植(IVF-ET)作为ART 划时代的里程碑。目前关于不孕与不育的争论已达成三个明确的观点。
观点一:不孕不育应当成为我国的重点研究领域之一。全世界约有 8 ,000 万对夫妇罹患不育,换言之,每十对夫妇中有一对不能生育。有人说,我国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计划生育与优生优育,不孕不育不应当作为重点研究领域。这个观点有失偏颇,一是因为我国不育症发病率约占育龄夫妇的10 % ,目前由于人们行为与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环境污染的影响,不孕不育的发生率有增高趋势。即使以10 %计算,也涉及相当大的一个人群。不能生育会对患者及其家庭带来一系列生理与心理的创伤,导致家庭破裂;二是因为生殖健康是每个公民的基本人权,我们既要为育龄夫妇提供安全、有效的节育技术,也有责任与义务帮助不育夫妇解决他们的生育问题。和谐社会的基础应当是美满与幸福的家庭。此外,不育是自然界的避孕试验,如果阐明某些原因不明不育的确切发病机理后,会有助于研制开发新的节育方法。一个正确及明智的研究战略应当是把生育、不育与节育三类研究有机结合三者相辅相成 相得益彰。
观点二:不孕不育不是一种独立的“疾病”,而是许多疾病中伴发的“共同症状”。不育当然是疾病状态,但与其他疾病相比,不孕不育不是一种独立的“疾病”。更为确切地说,不孕不育是在十分复杂的因素(包括遗传、环境、生活方式及社会诸因素,还有大量未被阐明的致病因素)作用下,男方、女方或男女双方多种“疾病”中,出现的一个“共同症状”——不育。对于这样一个多因素的“复杂系统障碍”,我们不能采用传统的一元一次线性代数的研究方法,而必须采用医学系统生物学的研究战略。要从目前经验型的不育诊治模式尽快走向询证医学模式。
观点三:不孕不育的研究策略必须是诊断治疗与预防及健康促进相结合。ART的出现为不孕不育夫妇带来了福音与希望。近二十多年来,ART 技术发展飞速,包括20世纪80 年代的胚胎与卵子的冷冻保存 (cryopreservation),1992年的卵胞浆内单精子注射(ICSI),20世纪90年代的着床前遗传学诊断(PGD),胚胎共培养技术,胚胎辅助孵化技术,睾丸精子吸取技术(testicular sperm extraction,TESA),未成熟卵母细胞体外培养技术(in vitro oocyte maturation,IVM)以及卵细胞核移植技术等,真可谓日新月异,自1978年以来,约有200 万婴儿借助 ART降临人世(不包括 AIH及 AID产生的孩子)。除此而外,ART技术崛起还大大推动了对人类配子与胚胎早期发育的研究,已成为当今干细胞(stem cell) 、体细胞克隆(somatic cell clone) 及 再 生 医 学 ( regenerativmedicine)研究的重要支柱。但也同时指出的是ART不一定是解决不育问题的首选、最佳及唯一和最终途径。ART同时还面临着许多技术与伦理方面的挑战。
总之,此项技术的出现推动了人类生殖科技向更高、更深层次发展,并超越了人类生殖本身的意义。
但是ART是一种比较昂贵的卫生技术,中国的基本国策是计划生育,卫生资源又十分紧缺,ART 在中国卫生资源的配置中应合理布局,以充分发挥有限卫生资源的最大效益。制订规范与准则的目的不是限制科学与技术的发展,而应为其健康发展提供宽松有序的支撑性政策环境。同时,规范与准则也不可能一成不变,必须不断审时度势、及时修订、逐步完善、与时俱进。